叩問「中國」:李歐梵與羅貴祥的一場文化研究思想交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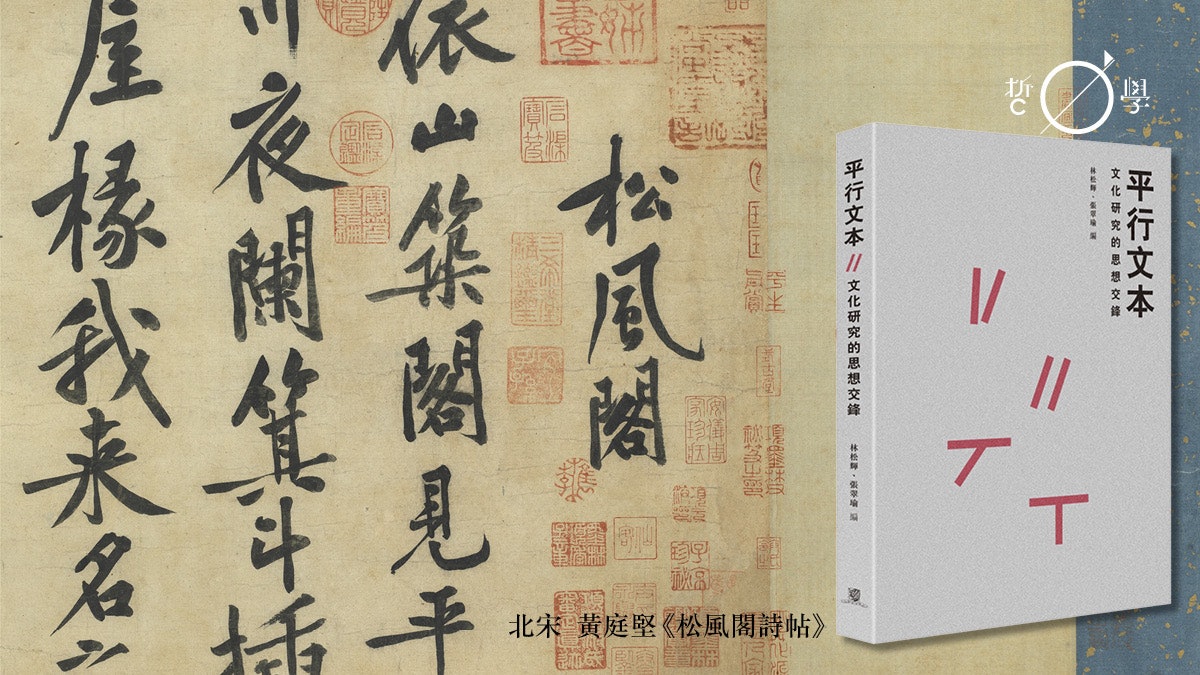
編按:「中國」究竟是一個相當晚近才出現的關於民族-國家的文化建構,還是一個儘管不斷變動卻其來有自的歷史實體?在叩問「何謂中國」的時候,我們應該反省近現代以來民族大一統、國家目的論的宏大歷史觀,如何掩蓋與抹除了關於「中國(中華民族)」所開展的種種細微操作,也應該考量怎樣避免用後現代國族建構理論架空歷史,落入虛無主義陷阱。李歐梵教授和羅貴祥教授曾針對《Beyond Sinology》和《何為中國?》兩個文本展開過一場文化研究的思想交鋒,嘗試探尋叩問「中國」的方式。本文為該次座談會的文字記錄,摘選自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物《平行文本——文化研究的思想交鋒》(原書第四至廿十九頁),獲版權所有者授權於網絡平台刊登,以饗讀者。讀畢本文後,歡迎選購原書閱讀完整內容。附註:主題圖片以「書寫」和「宋代」為創意概念,回應兩個文本各自的關鍵詞。
林松輝: 各位午安,歡迎大家出席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平行文本.交集對話」系列的第一場。我是林松輝,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首先,讓我介紹這個系列及今天論壇的講者和形式,然後展開討論。「平行文本. 交集對話」是一種新的對話方式,每次請來兩位重要的學者就近來出版關於特定題目的著作進行討論,對讀中文與英文寫成的文章。我們希望引發講者與聽眾、讀者與文本、不同語系的學術傳統之間的對話。因應香港獨特的語言環境,這個論壇將會以英語、普通話和廣東話進行。我先以英語開場,然後因應情況轉換語言。
我們為這場座談會挑選的文本分別是白安卓(Andrea Bachner)的 Beyond Sinology: Chinese Writing and the Scripts of Culture 以及葛兆光的《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下稱《何為中國》)。白安卓是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助理教授,她的著作的中文書名為《說文寫字:漢字書寫與文化的印跡》;葛兆光是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的特聘資深教授。
容我先簡單介紹兩個文本,以及我認為兩個文本對讀有趣的地方。相信許多聽眾現在手持兩篇序言的複印本,希望大家在活動前已閱畢文章。葛兆光的書是承接他在2011 年出版的著作《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 【注釋 1】 ( 下稱《宅茲中國》),他在此書一方面從歷史入手,建立對「中國」這個概念的理解,另一方面他回應其他學術傳統的著作,把「中國」問題放在整個東亞和世界的歷史來處理。《何為中國》延續《宅茲中國》的討論, 他以兩本書的篇幅探討這些問題。我個人認為,葛兆光其實是回應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的說法。在同名著作中【注釋 2】,杜贊奇提出:「歷史卻在不斷地鞏固着民族的神秘性,換句話說,就是鞏固民族是一脈相承的主體這一可疑的論斷。」【注釋 3】 所以杜贊奇認為自己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任務是要「揭示民族歷史的強迫性目的論,又要從歷史中拯救過去對於現在產生意義的方式。」【注釋 4】
在《何為中國》一書中,葛兆光直接回應杜贊奇的觀點,並於序言,也即是今天座談會的參考文章,指出從歷史來看「中國」是時有變化的概念,並不需要受限於後來的國家概念理解歷史。「『歷史上的中國,是一個移動的中國,因為不僅各個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歷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間邊界, 更是常常變化』…… 如果國別史的撰寫者,看到『民族』和『國家』本身的歷史變遷,就不會落入後來的『國家』綁架原先的『歷史』的弊病之中。」【注釋 5】
葛兆光作為一名歷史學者,提出宋代是形成「中國」意識的一個非常關鍵的朝代。白安卓則從書寫文字(writing script)的角度思考「國家」這個問題。白安卓認為西方對「國家」的想法於十九世紀末期才引入中國,是相當近代的事。她探討漢語裡聲音和文字的關係,援引大衛.達姆羅什(David Damrosch)有趣的說法,中國算是擁有國家的文字多於國家的語言,接着她反駁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關於印刷術造就「民族主義」的著名說法。她提出,「並非由語言來定義『民族國家』為擁有同一母語的群體」…… 而是「在『民族主義』此概念的咒語之下,因統一的需要先驗地決定了甚麼是國語,而甚麼被貶抑為方言。不是一個民族的公民真正使用的語言,而是強加的『國語的理想』雕琢了『民族共同體』的幻象」。【注釋 6】
有鑑於近來香港發生的事件【注釋 7】,這兩個文本正好提供一個機會,讓我們從歷史和語言的角度反思何謂「中國」和「中國性」(Chineseness)。正如白安卓所提出,「數位媒體革新和全球權力結構的重塑,此兩者的交滙衝擊了我們對中國文字和書寫的理解」。【注釋 8】 我希望接下來的討論, 秉持葛兆光於〈引言〉結語的想法:「至今,還有人不自覺地把政府當成了國家,把歷史形成的國家當成了天經地義需要忠誠的祖國,因此,產生了很多誤會、敵意、偏見。」【注釋 9】
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兩位非常優秀的學者進行對話,我們稱這樣的對話為不同語言和平行文本之間的「交集對話」。其實在座各位皆熟知兩位老師的著作,我實在不需要介紹他倆,在此僅點出兩位嘉賓與今天題目的關係。第一位嘉賓是香港中文大學冼為堅中國文化講座教授李歐梵教授。相信在座大家很熟悉李教授的現代中國文學和城市文化的研究,我認為他對中國思想史的識見將豐富今天的討論。第二位嘉賓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創意及專業寫作課程主任羅貴祥教授,他的近作是關於中國的少數族裔,我很期待他待會兒談談中國少數族裔的研究,還有以「亞洲」或「亞洲性」(Asianness)來與葛兆光的文本對話。今天的討論會如同讀書會,一個較為大型、和兩位專家一起參與的讀書會。今天的討論形式會是每位嘉賓先以十五分鐘分享對文本的看法,然後有十分鐘的時間回應對方的發言,再之後是台下提問和發言時間。我們先請李歐梵教授發言。
李歐梵: 我看到了許多熟悉的面孔,所以我就把這裡當成課堂討論好了。我很高興與羅貴祥同場。我希望自己這次講話的形式比較隨意,多鼓勵討論,所以沒有準備講稿。
林教授向我介紹白安卓此著作,在此之前,我沒有看過她這本書;但說到葛兆光的作品,我當然還是頗熟悉的。把這兩本書放在一起討論,我覺得是頗為聰明的選擇,這兩個平行文本就像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 的「對位法」一般,雖然它們運用的是不同語言、不同風格,但說到討論的觀點,兩者剛好是平行並列,有些地方能與對方對話,但當然也有不同之處,各自演繹出自身理論的音韻。我在此會用英文談白安卓的文本,因為它是英文寫成的,然後再換成普通話來談葛兆光。我知道羅教授會用廣東話,所以我們可以用三種語言來進行討論。
我建議大家至少要讀白安卓這本書的導言和結論, 藉此掌握其論點的重心所在。但這還是不夠,我希望你們也能夠讀讀另外兩章,如第一章「軀體學」(Corpographies)以及第二章「圖像學」(Iconographies)。一旦你們習慣了她大量採用抽象及深奧用詞的行文風格,接下來便可以繼續讀書中的其他篇章,分別名為「聲納學」(Sonographies)、「寓言學」(Allographies)以及「科技學」(Technographies)。正如篇章標題所示,這是一本非常沉醉於理論的著作,特別是法國理論,甚至連書名本身也是一個和理論沾上邊的雙關語:Sinology — 就是說, 作為一門學科的Sinology,以及作為一種表意系統的Sign-ology。白安卓的計劃明顯是野心勃勃:超越(go “beyond”)兩者。然而,書本封面的設計特色,卻是四個大的紅色中文字:「說文寫字」,以及十個其他作為副題的藍色字:「漢字書寫與文化的印跡」。這也是同樣深具智慧的做法。讓我們來試試解開其中的典故:它那標題的「原文」(ur-text)當然是來自許慎的經典作品《說文解字》,但白安卓這本書,卻又斷然不是那部經典中文字典的現代修訂版。副標題強調的是「漢字」,而不是「中文」,這大概是因為它想避免混淆現代中文白話的口語和書面語。她用了頗為少見的用詞「印跡」,而不是「軌跡」或是「蹤跡」,以強調印刷文化的「跡」(traces),這便立即令人聯想起安德森的名著《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的中心要旨,亦即如其副題所示,是為一 種「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的反思,印刷文化是其根源。這背後暗示的是,我們必須在中文書寫的問題上, 將民族主義一併引入討論。故此,我或許在這兩本書以外,也必須談談安德森的著作。
然而,我最希望在本書中探究的是:作者如何從經典漢學出發,將討論引申到現代民族主義?林教授已經引述她的結論,亦即對統一語言的追求,背後源自對現代民族主義的渴望。表面看來,這十分具說服力。若然如此,我們是否需要縱身投入龐大的法國符號學,用以反駁安德森?我認為白安卓著作的「副作用」同時就是她自身的知識專長— 的確是在於她的理論介入,藉着運用其一貫抽象的理論語言,她以另一種方式表達了自己在許慎書中的所得所感。讓我們來引述一句典型句子:「中文書寫,既是表意(signification),也是其反面,既奠定了意指物的抹除,也成了事物的救星:既是死亡的載體,也是容許物質性的幽靈纏繞着意義的一個中介。」【注釋 10】有沒有人弄得明白這句話的真正意思是甚麼呢?就算我們能夠將許慎從陰間拯救上來,他也絕對不會明白他的年輕美國門生究竟在想些甚麼。我們在此暫且淺嘗這句以及當中對法國符號學的着迷。可是,危機仍然存在: 這位作者似乎在理論語言中泥足深陷,以致她忘記了如何表述書寫漢字跟法國理論在根本上究竟有甚麼關聯。事實上,當中的確有關聯:正如周蕾(Rey Chow)在她一本書中曾指出,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在其《書寫學》(Of Grammatology)的討論中,或許曾以費諾洛薩(Ernest Fenollosa)和龐德(Ezra Pound)的著作為根基。但這是題外話。
另一個問題是,白安卓沒有完全處理中古時期文言文和口語這個同等複雜的問題,我不知道六朝詩歌曾否使用過任何方言,或是唐代詩歌應以廣東話還是普通話來誦讀。無論是否如白安卓所言,這也不必然指向語音的基礎。在西方理論,語言指的首先是聲音,而它的意義引申則自德希達所說的「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 centrism)。
如果你對理論有興趣的話,那麼白安卓的一些論點會十分有趣,特別是拉岡(Jacques Lacan)的部分。我知道,這裡有許多拉岡的信徒。白安卓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談及拉岡如何在他的一個研討會中,論及漢字的書寫:他舉了「人」這個字作例子,並問道:「這代表了些甚麼?為甚麼這是一個人的圖像?」然後他便說:「有頭部,也有雙腳,很合理,不是嗎?總是有些做夢的人。我寧願將它看成是胯部。」【注釋 11】白安卓自己便舉了這個例子,說明法國對於「軀體學」的迷戀其中包含的矛盾— 它暗指意義的載體以及對意義的捨棄,目的是,我猜想,去解構西方傳統的邏各斯中心主義。
於是,這便是白安卓討論符號和物質性的方式,她並沒有使用慣常中國人理解這個現象的方式,亦即援引四個漢字的基本類別:象形、會意、指事、形聲— 就是說,既是符號,也是聲音,既是圖象,也是語音。在處理法國理論的sign-ology 當中,我想她的著作已涵蓋了大部分的重要議題,但這在白安卓的書中只是其中一個部分,佔三分一左右;其他篇章論及作家及藝術家在當代華語地區的文化實踐。她非常深入地討論了侯孝賢的電影和陳黎的詩,並附上其他例子,以呈現中國文字和語音之間的關係的不穩定性和多元特質。於是,她便如大部分來自西方的中國研究學生一般,只對當代的現象感興趣,並似乎沒有耐性去處理關於歷史演變的背景資料。我對理論確實不太在行。我不能單在理論一環跟她展開辯論;故此,我會把她的理論擱在一旁,轉而評論她的「實踐」。
我的學術訓練源自歷史學,故此無論對錯,我總着迷於歷史。我扮演老派文化歷史學家或是「準漢學家」這些角色時,我便會問,她是否曾在中國語言的歷史演化的課題上,確實下過充分的研究工夫,包括中文書寫及口語。在我看來,若她要提出書中那些論點的話,這是不可或缺的背景。此書雖在象徵意義上深受《說文解字》的啟發,卻似乎對古典時期完全避而不談,而中國語言正是在中古時期不斷以不同方式經歷理論化及實踐。困難之處當然在於精通中國文言文,這也是早年歐洲漢學家(Sinologist) 所受的語言訓練,和獨有的「知識產權」,而這些當年活躍於西方世界學術領域的漢學家的數目,正在變得愈來愈少。我不是漢學家,但作為一位現代中國文學的學者,我無法迴避文言文在五四時期變成白話文的這個轉變。顯然,這是個老問題,但它一直吸引學者的目光。胡適固然有其說法,但現代白話文事實上並不是全然以口語為根基:換句話說,它既是口語,也是書面語,而兩者當中的微妙差別同樣是十分複雜。我們在此必須處理符號學及語意學,亦即符號及意義,因為現代中國語言包含了大量的複合字詞以及新詞,這構成了一種不同的調子。法國理論家如拉岡以及德希達對此並不感興趣;他們提及中文,目的最多不過是以此作為踏腳石,藉以通往他們自身的理論,如之前拉岡舉的「人」的例子或是德希達著名的「書寫」(écriture)論述。白安卓在書中選擇的是:徹底避開中國語言的歷史維度,並將整個議題置於現代民族主義的背景。很可惜,她只讀了安德森,而沒有讀葛兆光。當然,《何為中國》那時也還沒出版。
我認為,她透過引入民族主義這個大家較熟悉的主題,用頗具說服力的方式解決了一個語言的問題─也就是說,究竟是「語言先於民族」,還是「民族先於語言」這個問題。對於曾接受傳統漢學訓練的語言學家而言, 這不太重要,因為民族主義是一個外在的因素,處於內部演化的領域之外。我認為白安卓對跨學科充滿好奇, 這驅使她探索民族主義的因素如何進入了語言自身的複合體,但她在其語言實踐的部分,並沒有甚麼突破。我在此提出一個可能的背景:現代的白話書寫自身已然經歷了一段漫長的轉化。眾所周知,胡適追蹤了從宋代以降的「活的白話文」的書寫軌跡(因為他所有的例子均是來自書寫文字),特別是話本通俗小說。但各朝各代的白話並不都是一樣的。白安卓完全沒有提及過這一點或其歷史流變,我相信她沒有對文言中文進行過充分的研究,故此無法處理這個問題。所以我的建議是:如果你希望做得更好,那麼你便必須涵蓋整個領域,包括古典及現代。我同意,這是一件幾近不可企及的事。然而, 我們或許可以至少要求幾個例子,作為跟當代作品的對照?這或許聽來有點兒太過老套。白安卓選擇取道於更為現代的科技媒介(見第五章:「科技學」)。她在這方面的豐富知識確是令人印象深刻,但她似乎完全忽略了科技實際上的「物質性」自身——也就是說,中文打字機(發明者是林語堂)以及電腦程式。另一位女性學者、現任職於耶魯大學的石靜遠(Jing Tsu),在她新出版的著作《中國離散語境裡的聲音和書寫》其中一章中【注釋 12】,有論及這個議題,而白安卓也有將此書列入其參考書目中,但她明顯志不在此。
最後,我們必須談到安德森的著作《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當然,這是每個人都讀過的一本書,對吧?但你們有沒有讀遍整本書,留意當中細節?我想白安卓真的選讀了第二章〈民族意識的文化根源〉(“The Origins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以及第五章〈舊語言、新模型〉(“Old Languages, New Models”)。但在書中,安德森並沒有真正談論過中國,而只提及菲律賓、日本,以及其他亞洲國家。這是因為,安德森以這本「小書」一鳴驚人之前,是一位地區專家,一位東南亞研究的學者。縱使他受到本雅明等人(而非德里達及拉岡)的啟發,他的著作仍然是充滿着旁徵博引的歷史, 特別是當他討論位於美洲的歐裔海外移民的帝國(creole empires)之時【注釋 13】。正如其他大部分學者一般,白安卓隻字不提歷史背景,完全沒有談及「民族」及「民族主義」如何從帝國演化過來,一面倒只將焦點放在語言上。就算在這方面,我也會指出,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如果對統一「民族」的渴求孕育了民族語言(還是剛好相反?),那麼「民族語言」又是如何形成?它是不是只是一種書寫語言,受到印刷文化的影響,還是說,它既是書寫的,也是言說的, 既是視覺的, 也是聽覺的, 既是雜誌或報紙,也是電台及電視?的確,安德森深知這一點, 並在其後的修訂版中,加入了一些篇章,討論科技最新發展。
這裡說得太遠了,讓我們回到主題去,我們的着眼點仍然是中國— 跟白安卓的書一樣。白話文作為統一民族的語言,是口語、書面語,還是兩者皆是?誰在先、誰在後?這個民族語言是由現代文學產生出來,還是剛好相反?胡適自己曾經提出了一個口號:「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也作了很多論斷,但它們從來沒法平息任何爭議,到底孰先孰後─國語帶動新的文學,或是新文學作品塑造國語?讓我再舉一個擲地有聲的例子:為甚麼我們的民族語言應該要像官話?官話比較接近北京方言,但跟廣東話可沒有甚麼關係,而廣東話相信比較接近古代唐代的發音。而這又如何為當代詩歌及小說的書寫(更不用說電影對白)奠定基礎?只有想通這一點,我們才可以比較容易理解說廣東話的香港人關注的議題:普通話在哪一方面可以被視為是真正代表民族的語言,亦即正統的華語語系?這裡,我們的討論會更為接近一些關於意識形態的複雜問題。其中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但仍然蘊含重要顛覆意味的做法,來自現今的「華語語系」(Sinophone)理論,首先提出這個理論的是現在港大任教的史書美的一部著作—《視覺與 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注釋 14】。要注意的是, 這裡的關鍵詞除了是華語語系外,也包括視覺及認同, 而不是書寫及文字。相比書寫文化,視覺文化似乎正在當代世界中逐漸佔上風,故此我們倒不如忘記書寫文字吧?我將這個問題留給你們去設想和反思。我相信,華語語系一詞仍然比較接近聲音,而不是符號,而你們可以比較一下這兩本書,從而在當中理解它們如何在其政治及觀點上有所不同。一旦我們進入這些棘手的問題, 無論是理論方面還是其他問題,我實在沒法結束我的講話,所以我對白安卓的意見暫時先說到這裡。
談到葛兆光的這本書(各位如果看過此書的話),林教授講得非常對,他其實就是對抗杜贊奇的。因為杜贊奇那本書《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注釋 15】 使很多人很生氣,最生氣的就是研究中國歷史的人,覺得他完全以一種後現代的手法把中國歷史解構掉了。葛兆光寫得非常客氣,因為他在原來那本《宅茲中國》中很重要的一個論點就是:大家都說中國是天朝啦,天下啦,帝國啦;可是呢,他認為從宋朝開始,中國就有實際的版圖和國界的,一種「前現代」的民族國家的模型已經出現了,而且持續到了現在。這是他的很重要的一個觀點。他把他的這個「發現」(其實其他學者也提過,但沒有他講的那麼仔細)放在這本書裡面,就是說你們不要以為中國是二十世紀才產生現代中國,其實宋朝開始,特別是在南宋和遼國對峙的時候, 已經如此,雙方和談的條約已經言明是「兄弟邦」了(這是陶晉生的研究)。作為中國,除了版圖之外,當時也知道有其他國家的同時存在,而這些國家對「天朝」不見得都是臣屬關係,而是同等的關係。所以,從這個立場來講,葛兆光認為,大家不要以為中國作為所謂民族國家是現代性的結果,他認為後現代理論包括杜贊奇和安德森的理論,或者可以適用於印度,但不能適用於中國。因為中國這個模式,不僅指的是天朝,而且作為一個有實際版圖的國家,從宋朝到現在已經有將近一千年的歷史 。
當然我非常佩服葛兆光,他的學問非常好,你看他引用了這麼多的歷史材料,幾乎所有西方研究漢學的重要著作一本都沒有漏掉,這還不說,我更佩服他對於日本研究中國歷史和周邊國家的書一本也沒有缺少,在這麼一本篇幅很少的書中能寫出這麼多東西,實在了不起。也許這本書的長處就掩蓋了它的短處,我的問題就是:他是不是已經仔細讀過所有西方學者的著作?我的答案是不,這不可能。就像大家不可能把每一本外文書,包括杜贊奇的那本書,看得很仔細一樣。杜贊奇其中一個主要論點是「軟邊界」和「硬邊界」的問題,也叫做「邊疆和領土」(frontier and territory)。所以我覺得這個邊界的問題很重要。我的一個關於中國歷史的基本想法就是:那個延續性裡面一定有改變,你不能一直說延續到現在沒有改變。所以葛兆光說這是一個變動的中國,怎麼變動他卻沒有講清楚,特別是清朝的那一段。他批評歐立德(Mark Elliot),他批評柯嬌燕(Pamela Crossley),都是美國知名的清史專家,他說他們太着重清朝的滿洲傳統了,太着重清帝國的多元性,他認為西方漢學家似乎要拿清朝的多元性來反證和批評中國歷史學家的「大國沙文主義」,認為只有一個獨特的中國。
那麼台灣的學者呢,現在的研究趨向東亞地區歷史,因為台灣從地緣上可以和中國大陸、日本和韓國連在一起,形成「東亞」,當然台灣的地位在這個地區史的版圖中也提高了。然而葛兆光覺得,你們為了時髦,似乎連中國都忘了,所以我一定要講一個國家史裡的中國。我覺得他可能把這些西方漢學家的理論看得稍微粗漏一點,只是泛泛而論,沒有指出特別的細節。你把這幾種論述加在一起來看剛剛好,就好像是音樂,有的是重音,有的是輕音,你聽到重音而沒有聽到輕音,重音和輕音合在一起,再加上變奏,才變成一個旋律。當然,內面不乏互相衝突的和弦(dissonances)。另外,我覺得葛先生的著作還有一個理論的問題,我看他沒有把安德森看得很仔細,安德森講得非常清楚,他說不只是中國,歐洲國家在民族國家建立起來以前,也有一種帝國模式的大一統局面,如古羅馬帝國,語言文化很多元,但書寫的官方語言只有拉丁文。後來歐洲殖民南美和其他地區,構成新的「雙料帝國」(歐洲統治者與本地文化結合的帝國),為現代的民族國家鋪路。在這一方面,以上例子和中華帝國有何不同?這恰恰是美國的清史專家理論背後的問題,我認為值得比較一下。西方帝國沒有中國的「朝代更替」,所謂creole empires 也不見得那麼自以為「天下」。如果像中國那樣改朝換代的話,變成現代民族國家會否比較困難?這只是我胡亂猜的,天朝裡面的「中國」版圖,又如何想像?奧匈帝國之中有哈布斯堡王朝,也有匈牙利國,後來要求獨立的是匈牙利,而不是奧地利。所以,中國的「大國沙文主義」思想可能來自中華帝國原本很大的疆域,產生一種「天朝」想像,才會覺得中國版圖很大很大。可是不管你怎麼樣討論,我覺得nation-state 這兩個英文字中間的這條小線(hyphen)非常重要,它是nation-state,而不是nation/state,前者是分開的,後者是等同的。Nation指的甚麼呢?是「民族」,還是「國家」?中國表面上是多民族的國家,但除了元、清「異族」統治的帝國外,宋朝以後都是以漢族為中心。孫中山首先提倡革命時的口號是:「驅除韃虜,建立中華」,這個「中華民國」當然屬於漢族的。如何比較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清朝或民國時代裡各種少數民族所遭受的待遇?外國的學者反而對此特別注意,認為清朝知道自己是外族,所以對於其他民族(不只是漢族)比較寬厚,但也有等級之分,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呢?最初參照了蘇聯的各地區民族(nationalities) 管制系統,如果把這個制度和清帝國的政策參照比較, 恐怕基本上是沒有清朝那麼寬厚吧,不然的話西藏不會出問題,維吾爾、新疆也不會出這麼大的問題,這一個至今爭論不休的問題已經超出葛兆光這本書的範圍了。對不起,我的演講也已經超時了。
羅貴祥: 大家好。對不起,我知道有些聽眾聽不懂廣東話,但我說廣東話比較舒暢。我同意剛才李教授所講的,但我的看法是,中國和西方各自對中國是不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概念有很大的分歧,而這分歧正正可以在兩本書中印證。西方研究者總覺得,中國作為「民族-國家」(nation-state)是一個新近建構的概念。相反,中國學者傳統上認為中國是古已有之的「民族國家」,某程度上,是在歷史結構中發展出來的,而並非建構出來的。那我先說一下年輕學者白安卓的書,這是她第一本書,其實我只看過她一部分博士論文,她的博士論文基本上已有這些理論,但不是講中國,而是講馬來西亞,也講德希達和其他理論。這次她轉向講中國,她基本的框架,源於一次美國哈佛大學的華語語系會議,後來出了《全球華文文學:批判論文》【注釋 16】 一書。在書裡她想發展出一個概念,她就把這些意念放在中國的語系中,她在理論上相對熱心地處理了很多問題,但在歷史內容、歷史結構方面則比較缺乏,完全沒有討論古代,講中國大陸的例子也相對地少。因為她做中國研究集中在台灣,講陳黎、講夏宇和她的《腹語術》,或者講一些流亡海外的中國藝術家的作品,例如徐冰的《天書》,或者一些行為藝術。她的書裡用很多這類例子,但感覺有點跳躍,看不到一種歷史連繫,甚至感覺與歷史性脫鈎了。我認為這是一個最主要的問題,無論看「中國性」是一個本質,還是一個虛構的概念,在這上面兜兜轉轉,實際上卻並未找到較多的歷史證明。這是她的特色,但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缺點。
相對於葛兆光,他的歷史就比較豐富了,這應該是他的第二十幾本書。他有他獨特的關懷,所以才寫這本書。葛兆光為甚麼要寫這本《何為中國》?他在這一本小書裡不斷理性地翻查歷史,慢慢理性討論,但只要你細心看一看字裡行間,其實他在忿忿不平,不停的「所謂」:「所謂新清史」、「所謂後現代」、「所謂西方理論」。即使一些很認真研究中國歷史的西方學者,用一個「所謂新清史」的角度來研究…… 如果大家稍微接觸過一點歷史背景,1980 年底柯文(Paul Cohen)發表研究,他是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的學生。費正清研究中國,傾向以中國作為回應者(responder)的結構:西方的科技、現代化來到中國,中國會怎樣回應西方現代化。柯文師承費正清,但他意識到他不能這樣研究中國,於是他提出以中國為視角來研究中國。有趣的是,西方人提出以中國中心研究中國,這樣慢慢發展出後來提出「新清史」的人,可能是他的學生或者是受到他影響的人。研究中國歷史時,如果你要看清代的歷史,是不是應該從清朝、從滿清族的角度來研究清代歷史呢?或者,清朝應不應該有「清代歷史」?因為從傳統的中國歷史來講,清朝永遠只是一個朝代,必然是在一個以漢人為主的中國歷史裡的一部分。「新清史」的意思是,研究者會用很多滿文的材料,來講清代歷史到底是怎樣的。這一點葛兆光似乎就做不到。漢人寫的清史,永遠是清朝入了關之後女真族漢化了,但從「新清史」學者的寫法來講,清朝統治中國,用了一個所謂「漢化」(sinicization)的策略, 但清朝統治者從沒被動地受到「漢化」,只是利用這個手段來管治漢人,再用類似手法管治其他地方。譬如,對西藏,就談活佛和藏傳佛教;對西南苗和新疆、蒙古分別用不同的方法和制度。所以清朝對漢人當然說自己「漢化」,表面上說尊重儒家,但如果根據「新清史」的研究,清朝其實很有意識不受「漢化」。為甚麼滿人根源的東北地區這麼多年來,都封鎖了,不讓漢人進入;待晚清受到了列強威脅後,才讓漢人進入,以鞏固國防。所以我覺得「新清史」提供了一個很新、很不同的角度來研究中國歷史。
但這些角度正正不符合葛兆光的史觀:中國作為民族國家其實由宋代已經開始,一直傳承到現在,是一個持續。「新清史」對葛兆光本身的位置和論點有很大的衝擊,所以他不承認這樣的研究。話雖如此,由宋代開始比較強調華夷之別,不接受外族,近代中國開始形成, 以上觀點其實不是由葛兆光最先提出的,七十年代已有外國學者提出類似的問題。葛兆光也引用八十年代,一位叫羅薩比(Morris Rossabi)的學者編的書《鄰國中的中國:中國與鄰國,十至十四世紀》【注釋 17】。七十年代已有人提過宋代的愛國主義,因為宋受到較強大的外族威脅,於是產生了一種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葛兆光提出的不是特別新鮮的觀點,但問題在於,宋代很強調華夷兩者的分別,這可能只是中國傳統對外族的一種比較普遍的思想,不一定能構成現代意義下的「民族國家」。反過來說,「民族國家」的理論是現代化的其中一個產物,未必一定要完全接受現代西方對「民族國家」的論證。
所以亞洲國家怎麼接受「民族國家」這個政治形式, 甚至變成世界其中一個合法的身份,然後和其他「民族國家」競爭?這是一個世界性系統理論的概念,如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講的,如果你拿不到「民族國家」的一個執照,你就沒有權和其他「民族國家」競爭了。這個模式來自歐洲,十七世紀開始,這就是歐洲一個互相競爭的合法機制,因為這肯定了一個現世的權利。以前所爭取的權利如果不是強調領土主權,就會是精神、價值觀和文化層面的征服。但今天提出這個「民族國家」,在當時就平衡了歐洲內部的競爭,令歐洲各個國家的競爭有個限度,即是它的主權也只能在自己領土範圍以內。當然,大家還是會發動戰爭,互相侵略, 領土不斷改變,但起碼會「尊重」這個概念,不會有統治整個歐洲那種太大的野心。其實這是一種控制、爭取資源和其他權利的競爭機制。接受「民族國家」需要有一個很重要的意識形態,就是民族主義。在現代,中國沒有選擇,不接受就會被人淘汰。我們讀梁啓超、康有為的著作,知道若不接受(民族國家的話),你就根本沒資格在現代世界上有自己的聲音。日本人也曾透過民族主義來侵略中國,認為中國有太多民族了,根本不是一個典型的「民族國家」,不如與日本合併,由日本教導做一個真正的「民族國家」。葛兆光作為一個中國人,即使他不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但也難免會有強烈反應。他已經盡量嘗試心平氣和地講一個問題,但是他發覺在很多事情上,若挑戰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觀念,就像犯了天條死罪,所以他要起義、辯駁。他找尋種種方法去講一個問題,在書裡面不斷重複歐洲的概念不適用於中國,但問題在於,國家主義論述不是其中一個歐洲概念嗎?為甚麼用這一個歐洲概念,而不用其他呢?雖然他反對把問題政治化,但似乎又很難擺脫政治化,因為當他強調中國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時候,其實已經十分政治化了。
他後來談到,他思考問題是針對現實的當代中國, 現今的中國政府的權力似乎非常大,這個正是「民族國家」所面對的問題,所有事情都很容易變成強調國家利益,所有其他事情都要為此犧牲。雖然「民族國家」裡有所謂「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主權應該屬於人民,但這反而被利用為維繫國家利益的口號。所以當他這樣講的時候,他究竟有沒有在針對當今中國?一些現今中國的主流論述,把這種「民族國家」的論述更加合理化,葛兆光並沒有在書裡處理以上問題。其實這樣很危險,像在幫當權者製造很多合理的管治理由。我覺得他在這方面不夠警覺。為了要滿足中國自宋代以來便具備了民族國家規模的一個歷史條件,他沒談及語言的問題。白安卓那本書正正補充了這一方面,如果白安卓做多點中國古代歷史的研究,我想會更加容易看到葛兆光這本書的此項不足。我不是一個歷史學家,但我仍然覺得他強調的地方有些不盡完善。他在書中有提到新疆建省的問題。我們知道,新疆建省有很複雜的歷史背景, 他只提到部分資料,卻沒有把資料連結在一起。平定新疆是1759 年,但新疆建省是1884 年,距離一百多年, 為甚麼隔了這麼久呢?一方面,正如剛才所說,清朝素來都是「分而治之」,根本沒興趣將所侵略的土地,變成一個大家所謂的「統一的帝國」(unified empire)。清朝想「分而治之」,主要原因是他們覺得這樣最易控制、最為安全,最好所有漢人不要聚居新疆,否則民族混合在一起,容易釀成動盪。但是到了後期,才因種種原因把新疆開放,其中一件事就是「回亂」。左宗棠作為一個漢人大官,提議用中國傳統的「行省制」,把新疆納入省,方便管治,也可以平定回民的騷亂,回亂一直騷擾了清代幾十年,終於用建省的方法平定動亂,清朝也就接受了建省。另一個原因是受到俄羅斯的威脅,建省以後,新疆要讓更多漢人走進去,作為屏障來對抗俄羅斯的侵入。所以,新疆建省正正代表帝國開始解體的危機,而不是建立統一大帝國的榮譽。這個極其關鍵的影響,葛兆光完全沒談及,但他一定知道,但他似乎故意忽略了這件事。然後清朝開放蒙古讓漢人進去,也引起了很多蒙古人的憤怒,蒙古人問:為甚麼清廷要讓漢人來搶我們的土地?但這些措施都是因為要對抗俄羅斯和日本, 那時她們開始對中國邊疆有所圖謀,所以清朝一定要讓漢人進去建立一個緩衝區(buffer zone),以對抗外國勢力,清代解體的契機便由此開始。我就先說到這裡。
座談會於2014 年10 月10 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8 號演講廳舉辦。
本次座談會參考文章
Andrea Bachner, “Introduction”, Beyond Sinology: Chinese Writing and the Scripts of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17.
葛兆光,〈導言〉,《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1–32。
注釋
1.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台北:聯經出版,2011)。
2.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3. 原文為“History has often worked to secure the mystique of the nation, or in other words, its dubious claim to an evolving, monistic subjecthood.” 中譯參考杜贊奇,王憲明、高繼美、李海燕、李點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15。
4. 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頁16。
5. 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30–31。
6. 原 文 為 “It is not language that defines a nation as a community of native speakers . . . the need for unification under the spell of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predetermines what can count as a language, and what will be relegated to a dialect. Not the real languages of a nation’s citizens but the imposed ideal of one national language crafts the illusion of national community.” Andrea Bachner, Beyond Sinology: Chinese Writing and the Scripts of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5.
7. 指2014 年9 月下旬香港發生的「雨傘運動」。
8. 原文為“the confluence of the digital media revolution, and the reshaping of the global power structures impact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script in particular and of writing in general.” Bachner, Beyond Sinology, p. 14.
9. 葛兆光,《何為中國》,頁32。
10. Bachner, Beyond Sinology, p. 33.
11. Bachner, Beyond Sinology, p. 32.
12. Jing Tsu,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3. Creole 意指多種語言混合形成的混合語,也譯作克里奧爾語。於《想像的共同體》中文版,譯作「歐裔海外移民」,專指這群海外移民建立民族國家的情況。見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1999),頁93。
14. Shu-mei Shih,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中文版: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台北:聯經, 2013)。
15. 見註釋 2。
16. Jing Tsu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al Essays (Leiden: Brill, 2010).
17. Morris Rossabi ed.,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平行文本:文化研究的思想交鋒》
© 香港中文大學 2018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出 版: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文化研究中心香港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梁銶琚樓2 樓212 室電話:+852 3943 1255
電郵:cuccs@cuhk.edu.hk
網頁:www.cuhk.edu.hk/crs/ccs
編 輯:林松輝、張翠瑜
校 對:譚以諾、李豐宸、葉寶儀、鄒文君、高俊傑
翻 譯:雷浩文
協 力:何杏園、林詠雅、董牧孜、何哲瑩設 計:陳素珊
發 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版 次:二零一八年十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定 價:港幣88 元
國際書號(ISBN):978-988-79285-0-8
建議分類:(1)文化研究(2)文化評論
Printed in Hong Kong
關於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於2014年8月成立文化研究中心,前身為文化與發展中心。文化研究中心致力推動文化研究領域的研究、學術交流與推廣工作,舉辦多個國際學術會議、論壇、工作坊和學術講座,連結國際與本地的學術討論。現時中心的研究計劃關注社群藝術發展。自2015年,為亞際文化研究機構聯合會成員。
《01哲學》,哲學入門,深入淺出,更好地理解,更好的邏輯。立即下載《香港01》App:https://hk01.onelink.me/FraY/hk01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