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從法治國到安全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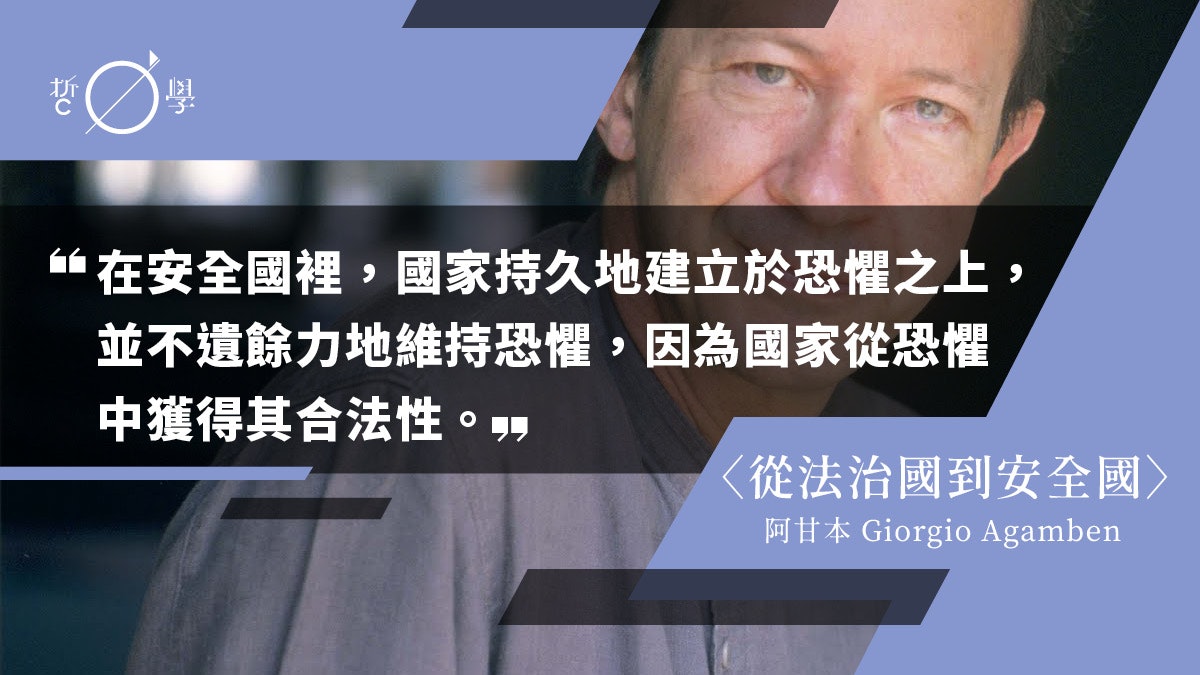
譯者|孫健,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碩士校對|aowen,巴黎第四大學哲學碩士本文譯自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的《De l’Etat de droit à l’Etat de sécurité》,原刊於《世界報》(Le Monde)2015年12月23日。
前言
對於義大利哲學家阿甘本而言,緊急狀態並不是保護民主的盾牌,相反,它總是與獨裁相伴。
如果不把緊急狀態放在我們熟悉的國家模式劇變的語境中,我們便無法理解,法國將其延長(至二月底)的真正利害。首先應當揭露不負責任的政客的謊言,他們聲稱緊急狀態是民主的盾牌。
歷史學家非常清楚,真相恰恰相反。極權政府正是通過設立緊急狀態這一途徑在歐洲生根發芽。在希特勒奪取政權之前的幾年,魏瑪民主社會黨政府便曾頻繁地求助於緊急狀態(即德語中的例外狀態),我們可以由此認為,早在1933年之前,德國就已經終結了議會制民主。
然而,希特勒掌權之後的首要行為,便是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並且再也沒有撤回。我們為納粹在德國犯下罪行而沒有受到制裁感到震驚,卻忽略了這些行為曾是完全合法的,因為德國當時處於緊急狀態下,個人自由被懸置了。
我們不能預言,相似的情景在法國不會重現:可以毫無困難地想像,當社會黨政府使公民習慣於緊急狀態之後,一個極右政權便可利用它達其目的。在一個緊急狀態被延長的國家裡,員警行動逐漸取代司法權力,我們可以預料,公共機構將快速且不可逆轉地退化。
維持恐懼
當下尤為明顯的是,緊急狀態被列入將西方民主推向如今稱作「安全國」(l’État de sécurité)的進程之中。「安全」這個詞在政治話語中如此常見,以至於我們可以毫無顧忌地說,「安全理性」已經取代了過去我們談論的「國家理性」。然而,對於這一新型政府形式的分析卻乏善可陳。由於安全國既不屬於法治國(l’État de droit),也不屬於傅柯所說的「規訓社會」,這裡便有必要做一些界定,以便得出一個可能的定義。
英國哲學家霍布斯的模式對政治哲學有著深遠影響,在這個模式裡,權力通過契約移交給君主,這份契約預設了相互的恐懼以及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國家便是來終結恐懼的。在安全國裡,這一模式顛倒了,國家持久地建立於恐懼之上,並應不遺餘力地維持恐懼,因為國家從恐懼中獲得其根本功能和合法性。
傅柯已經指出,當「安全」這個詞首次出現在法國大革命前重農主義政府的政治主張中時,重要的並不是預防災難和饑荒,而是任其發生,以便隨後能夠治理災難並將其引向人們認為有益的方向。
毫無司法含義
與之類似,當下涉及的安全,並不在於預防恐怖主義行為(況且這極其困難,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安全措施只有在事後才有效,而根據定義,恐怖主義是一系列首發事件),而是力求與人建立一種新型關係,一種籠統的、沒有限制的控制關係,其中尤其重要的部署,是針對公民資訊和交流資料的總體控制,包括獲取電腦內容的所有資訊。
這樣做的危險,首先是有可能持續演化,誕生出恐怖主義與安全國之間系統性的關係:假設國家需要恐懼來使其合法化,就應當製造恐懼,或者至少,不阻礙恐懼的發生。一些國家便是如此,他們的外交政策扶持著我們在國內打擊的恐怖主義,並且與已知的恐怖組織資助國保持著良好關係,甚至向其銷售武器。
其次,相當重要的一點,是公民和人民政治地位的改變,他們曾被認為是最高權力的擁有者。在安全國中,一種可以稱之為公民逐漸非政治化的的趨勢不可抑制地出現,公民的政治生活縮減為選舉投票。這一趨勢因為納粹法學家曾將其理論化而更加令人不安,他們將人民定義為首先是非政治的元素,而國家應當確保其安全和發展。
然而,根據納粹法學家,僅有一種方式能將這個非政治元素政治化:通過同樣的祖先和種族,將人民與外國人和敵人區分開來。這裡並不是要將納粹國和當代的安全國混淆:需要理解的是,如果我們將公民非政治化,他們就會一直處於被動狀態,除非使用針對外國敵人的恐懼來鼓動他們,尤其當這些外國敵人並不僅僅來自外部時(就像德國的猶太人,法國今日的穆斯林)。
不確定性和恐怖
應當將剝奪雙重國籍者國籍的可怕計畫放在這個框架下考量,它讓人想起一條1926年的法西斯法令,關於剝奪「義大利公民身份中的的劣民」的公民權,以及關於剝奪猶太人公民權的納粹法令。
第三點,其重要性也不容低估,便是在公共領域建立真理和確定性的標準發生了巨大轉變。在對恐怖主義罪行的報導中,細心的觀察者最先注意到的,是對建立司法確定性的全面拋棄。
眾所周知,在法治國中,罪行只能通過司法調查來證實,而在安全國的範例下,我們應當滿足於員警以及依附於它的媒體的言論——也就是說兩個向來可信度極低的機構。事件的匆忙重建異常模糊,有著明顯的矛盾,有意規避核實和造假的所有可能,往往更像是流言而非調查。這意味著,安全國必須保障公民的安全,便需要公民始終處於對其威脅者的不確定性中,因為不確定性和恐怖並駕齊驅。
在11月20號頒佈的緊急狀態法案中,我們便能感受到類似的不確定性,援引如下「有嚴肅理由認為,每個人的行為都有可能構成對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威脅」。很明顯,「有嚴肅理由認為」這一用語完全沒有司法含義,它給了「認為」的人以裁定權,可以在任何時候對任何人使用。或者說,在安全國中,這些不確定語式成為準則,而它們之前一直被法學家認為有違法律確定性原則。
公民的非政治化
類似的模糊性和不準確性在法國政客的宣言中重現,他們認為法國處在對抗恐怖主義的戰爭中。一場對抗恐怖主義的戰爭在字意上便是矛盾的,因為戰爭狀態正是通過能夠明確識別敵人來定義的。與之相反,在安全國的觀念中,敵人應當是模糊的,以便於任何人——內部的,同時也有外部的,都能夠被認為是敵人。
維持普遍恐懼的狀態,將公民非政治化,拋棄所有法律確定性,便是安全國的三個特徵,已經足夠讓人不安。因為這意味著,一方面,我們正逐漸轉入的安全國做的事情與它承諾的相反——如果安全意味著擔憂(sine cura)的缺席,安全國卻在維持恐懼和恐怖。另一方面,安全國是一個員警國,因為借由司法權的消退,它將員警自由決定權的空間系統化,在緊急狀態成為常規的情況下,員警行使著越來越多的主權。
通過逐漸將公民非政治化,安全國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強勢恐怖主義,它超出了我們所熟知的政治領域,指向一個不確定的區域,當中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混淆,我們無法定義其邊界。




